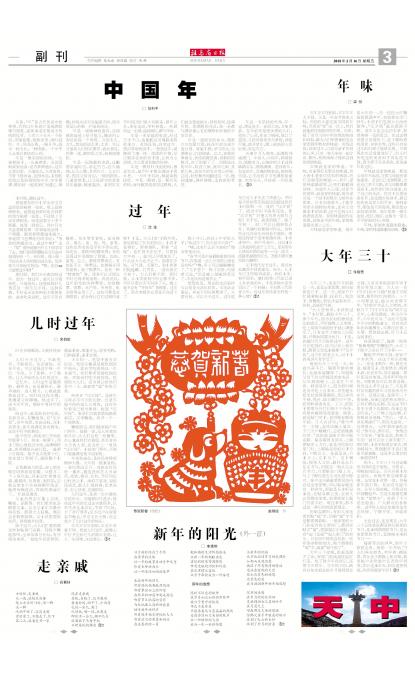□ 沈 淦
小时候,最盼过年。
看到现在的中小学生在文具盒的里层贴着一张纸,纸上画着课程表,就想起我那时也在同样的地方贴着一张纸,不过纸上可没有课程表,而是画着五十多个圆圈。每周一到校后,我打开文具盒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涂掉一个圆圈。眼看着圆圈越来越少,我就眉飞色舞地对同学说:“等我的圆圈涂完,就过年啦!”这一“招”很快就被另外几个同学学了去,他们也将圆圈贴在文具盒内每周涂掉一个。有时候,课上到一半还会有人悄悄地回过头来,低声却又兴奋地对我说:“喂,还有××天就要过年啦!”
那时候,我们天天都在盼过年。因为一到过年,就可以尽情地吃、尽情地玩,还能得到好几角甚至一两元压岁钱,这种待遇,平时是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的。就拿吃来说吧,过年不但有糖果、花生等零食吃,还有糕点、馒头、鱼、肉、鸡、蛋等。这些东西有的是平时不供应的,如花生、蒸糕用的糯米等;有的是因过年而增加了数量,如肉、蛋等。总之,都得凭票供应,有的还不止一种票证,如蒸馒头用的面粉,除了粮票外,还有一种“特富粉”券,凭券可以买到比平时白得多的面粉。再说说玩,过年前发的各种票券,如食糖票、肉票、水产券、专用券、机动券等全用上了,这些可都是有期限的,谁舍得让它们过期作废呢!于是,大人们忙于购年货,到处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小孩子也得忙,帮着排队,帮着“运输”,也忙得不亦乐乎。只要到大年初一,就可以尽情地玩了,什么活大人也不让干,揣着压岁钱,买气球、买爆竹,和小伙伴们捉迷藏、打雪仗,一直玩到正月初十,大人们都不管。那时候,从小学到初中作业都不多,平时只要白天不玩昏了头,晚上就不会有“开夜车”的现象。过年了,那点寒假作业更是不在话下了。
数十年后,我问上中学的儿子:“快过年了,你兴奋不兴奋?”
“咦,这有什么好兴奋的?”他奇怪地反问。
“春节可是中国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你难道一点儿兴奋的心情也没有吗?”“噢,早上可以睡睡懒觉了。”儿子想了一阵才回答,可接着又说,“但是晚上却睡得更迟了,不是玩而是做作业。”
想想也是,现在的生活条件与以前是无法比拟的,买生活必需品,再也不用任何票券了,只要有钱,可以天天过年。过年吃早已对儿子失去了诱惑力,平时每月给的零花钱就远远超过我们小时候那一年一度的“压岁钱”了。既然平时不缺零花钱,那“压岁钱”对他又有多大吸引力呢?至于玩,就更别提了。除了年初一、初二可以让他放松点外,其他时间都得写作业,各科作业压在肩头玩得也不痛快,寒假还得请个老师替他补课。小学进初中,初中升高中,往往1分之差就得花成千上万元,还有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高考……这一波又一波越来越强的压力,怎能不磨灭他玩的兴趣呢?
父子两代对于过年,竟有如此截然不同的感受。如今,儿子早已工作即将成家,我的小学、初中同学,他们的第三代也已进入小学或初中,于是我脑中忽然冒出了一个问题:不知第三代的青少年,对过年将怀着怎样的一种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