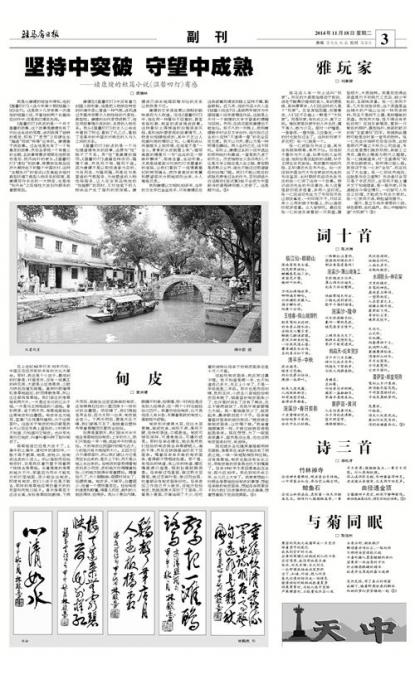□ 曹天啸
在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革命。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最深刻的印象是,村里很穷,没有一间真正的砖瓦房,大都是土坯淮草房,少数为砖包后墙瓦接檐。盖房时砌墙得轧淮草地起坯,封顶得散淮草,所以庄庄都有淮草地。我们娄庄的淮草地有两大片,一片是庄东北的三尖子地,一片是与王岗相连的八亩地。春秋两季,连下两天雨,淮草地里就生出黑甸皮和白蘑菇。甸皮学名为地耳,蓝藻门念珠藻科植物,分不出根茎叶。这些关于甸皮的知识都是我长大以后在字典上查到的,小时候并不知道,只知道叫它甸皮。也许早先是叫它地皮,叫着叫着叫转了就叫甸皮了。
哥哥姐姐已经是大孩子了,上高中的上高中,读初中的读初中,一般不再干割草、剜菜、放牲口、拾甸皮这类的小活儿。所以每到雨后拾甸皮时,总是我㧟着竹筐子领着两个妹妹去淮草地。长着高高的淮草的地方不行,那里因为雨水不能充分的打湿地面,很少能生出甸皮。即使有甸皮,我们小孩子也是不敢去,那样的淮草地经常扔着夭折的死婴和死牲口娃子。春天淮草茬子还没长高,深秋淮草刚刚割掉,下两天雨后,就能生出密密麻麻的甸皮,还有稀稀拉拉的小圆顶房子一样形状的白蘑菇。雨后晴了,我们得起老早去拾,因为太阳一出来,甸皮就会变小。下两天雨后,要是天还不晴,我们都等不及了,就披着白塑料布带着草帽顶风冒雨去捡拾。
如果是星期天,我们就半天半天地去淮草地捡拾甸皮;上学的天儿,我们只能趁一早一晚,或趁中午时候去拾。大的甸皮比民国时的银元还大,小的就只有大拇指甲大小。正因为它分不清根茎叶,所以我们都认为它是凭空长出来的,是天上下的,而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拾甸皮的姿势得看甸皮的多少而定,多的地方你得蹲着捡拾,少的地方就得半弯着腰拾。蹲着拾久了,大小腿酸麻;弯腰时间长了,后腰疼痛。甸皮多,不稀罕;白蘑菇少,捡着一个便欣喜若狂。捡拾甸皮的速度和数量,得看人而定,麻利的人就捡得快、捡得多。我从小患白内障,眼睛不利索,捡得慢,同一时间总是没有别人捡得多,但一两个小时也能捡拾三四斤。我喜欢捡拾甸皮,比干其他活儿有兴致,手摸着柔软的甸皮心里就格外舒服。
甸皮形状像黑木耳,但比木耳更嫩,做成吃食,润而不滞,滑而不腻,色味形俱佳,口感甚佳。甸皮可焯后凉拌,可清煮做汤,可爆炒成菜。那时母亲还健在,她总是把我们捡拾的甸皮拣去杂草硬棍儿,淘洗干净,然后在铁锅里油炒后下豆面条。喝着母亲亲手做的甸皮面条,香得都不想咽进肚里。那个香,有鸡汤的味道,有山珍的味道,嚼在嘴里满口溢香,咽到肚里脏腑流香。母亲做过鸡蛋面,做过煎水豆腐面,做过芝麻叶面,做过肉丝面,吃着都没有甸皮面条好吃。后来参加工作自己开火做饭,没地方捡拾甸皮,我就泡黑木耳炒了下面条,尽管是小麦面,尽管油倒了不少,但吃着的滋味比母亲下的甸皮面条总差十万八千里。
说起吃甸皮面条,我还哭过鼻子哩。我不知道是哪一年,也不知道自己多大,反正上小学了,不是一年级就是二年级。那天也是雨后初晴,我和玉洲、小成去八亩地捡拾甸皮回来晚了,锅里留的甸皮面条少了,也许是时间长了没有了稀汤,反正不够两碗饭了,而我平常都要喝三大碗。我一看锅里饭少了,就哭起来,鼻涕眼泪流个不尽。母亲端着盛好面条的碗劝我说:“晚饭娘还做甸皮面条,让你喝个够。”我耸着肩膀痛哭一阵,才接过碗狼吞虎咽起面条来。现在想想,为了一碗面条哭鼻子,固然是没出息,但也证明甸皮面条好吃、有滋味。
现在城乡各处建房盖楼都用砖瓦楼板,淮草早在20多年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一块一块地犁掉改种庄稼。没有淮草地,甸皮也就没有生长之处,用甸皮做的饭食再也吃不到嘴里了。母亲1985年冬季因患高血压去世,距今近30年。我也到知天命之年,女儿已上大学了。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去淮草地捡拾甸皮的事情,想起母亲做的甸皮面条,想起母亲疼爱孩子和为我们日夜操劳的点点滴滴,想着想着就不觉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