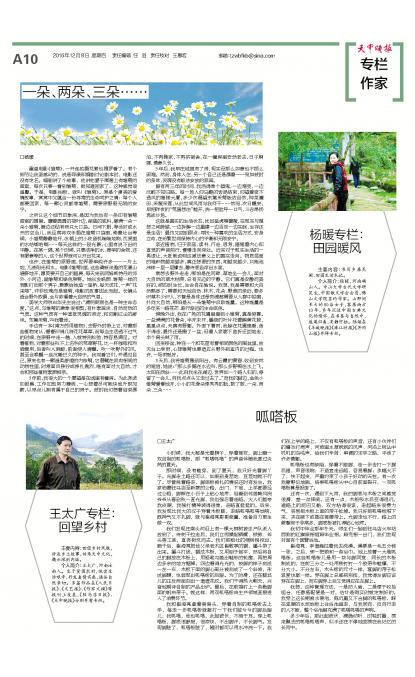一朵、两朵、三朵……
□杨暖
重温电影《雏菊》,一并连拍摄花絮也搜罗看了。有个细节让我蛮感动的,说是导演和编剧讨论剧本时,电影还没有定名。编剧讲了个故事,他讲他妻子围裙上有雏菊的图案,每次只要一看到雏菊,就知道回家了,这种感觉很温馨。于是,电影拍板,就叫《雏菊》。原是个凄美的爱情故事,冥冥中又蕴含一份寻常的生命呵护之情:每个人都要回家,每一颗心灵都像雏菊,需要原野般无限的安宁。
之所以这个细节印象深,是因为我也有一条印有雏菊图案的围裙。镶着圆圆的荷叶边,湖蓝的底料,撒满一朵一朵小雏菊,裙边还贴有两只大口袋。日间下厨,等汤好或水开的空当儿,我经常将双手插在雏菊口袋里,倚着灶台等候。小雏菊静静地开,冰箱上的小收音机嗡嗡地响,瓦煲里的水咕嘟咕嘟……每天这样的一段光景,心里有说不出的平静。在某一隅,某个时候,只要洁净的水、简单的食物,还有愿意等的人,这个世界就可以开出花来。
也许,在雏菊的原野里,世界要单纯许多——一片土地,几缕阳光和水。电影《雏菊》里,这些清新淡雅的花漫山遍野地开,惠英要开自己的画展,每天来到阿姆斯特丹的郊外、小河边,画雏菊和绿色原野。她长发皓颜、雏菊一样的背影打动那个男子,默默给她造一座桥,每天送花,一声“花来喽”,并非玫瑰而是雏菊,电影的故事因此而起。长镜头适合野外取景,全片弥漫着大自然的气息。
美学大师
手边有一本《南方药用植物》,去野外时带上它,对着那些植物来认,慢慢识得几株花花草草,而每当生活透不过气的时候,在原野中走一趟,人就特别松弛,特容易满足。对着植物,对着那些叫不上名字的荒草野花,比一杯咖啡和烈酒管用,后者叫人麻醉,前者使人清醒。吹一吹野外的风,甚至会唤醒一些沉睡已久的种子。我观看它们,并遇见自己,原来也有一颗温柔舒缓的内核啊,它潜藏在灵肉相间的动物性里,时常面目狰狞或挣扎激烈,唯有面对大自然,才会和那些植物素颜相亲。
5年前,我很大的一个愿望是在城里有幢房。为此奔波如困兽,工作加班努力赚钱,一心想着尽可能快地升职加薪,以早点儿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彼时我幻想着结束漂泊,不再搬家,不再挤宿舍,在一幢房里安然老去,日子婀娜,情意久长。
5年后,我早在城里有了房,现实没那么如意也不那么困难。然而,身体入住,另一个自己还是漂着——宛如彼时的身体,灵魂没有皈依安放的家园。
曾有两三年的时间,我活得像个酒鬼,一边难受,一边沉醉不知归路。每一场人仰马翻的饭局结束,仰望着密不透风的高楼大厦,多少次渴望东篱采菊皈依自然,种菜灌田,采薇采莲,从此世间风雨与我何干……然而,次日醒来,早把昨夜的“荒唐想法”抛开,洗一把脸呼一口气,斗志昂扬再战沙场。
这就是真实的生活状态,犹如猛虎嗅蔷薇,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跨越,一边拆解一边重建一边否定一边实践,生存还是生活?最终又回到原点:寻找一种喜欢的生活方式,安身立命,在纷繁世间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无限安宁。
亲近植物,归于家庭,读书、行走、思考,跟随着内心和直觉的声音前行,慢慢走向深处。近来对于现实生活的一再退让,大抵能说明这减法意义上的真实走向。物质层面的堆积物越来越多,真正想要的东西,却越来越少,只能泡沫样一层一层撇去,静待底色浮出水面。
常想去野外走走,哪怕是在河畔、草地坐一会儿,面对大自然的草木枯荣,总有无边的宁静。它们真是安静而美好的,顺四时生长,生命自在愉悦。我想,我是需要和大自然熟悉了,需要和天地自然、林木、花朵、野草的亲近,要多识草木少识人,不管是身体还是灵魂都需要从人群中抽离,扑向大自然,哪怕是从一朵雏菊中汲取能量。这种能量是多年来一路苍茫、渐行渐远的生命底色。
傍晚外出,我在广场的花圃里看到小雏菊,真是惊喜。一盆满满的花骨朵,半开未开,墨绿的叶片托着鹅黄花苞,星星点点,天真有野趣。外面下着雨,我躲在花圃里看,舍不得走,最终还是搬了一盆,沿着人家廊下曲折迂回地走,半个肩头淋了雨。
回来移盆,种在一个和花苞有着相同颜色的陶盆里,放天台上淋雨,心想雏菊也要适应从野外到室内的过程。也许,一场雨就好。
3天后,我将雏菊搬到阳台。有云霞的黄昏,收到安然的短信,她说:“那么多鹅在水边叫,那么多野鸭在水上飞。太阳在西斜……此刻我坐在湖边,世界如一个路人似的,停留了一会儿,向我点点头又走过去了。”而我的脚边,金色小雏菊慢慢地开,小小的花骨朵像秀秀的脸,数了数,一朵、两朵、三朵……

杨暖专栏:田园暖风
主要内容:书写乡居见闻、田园生活札记。
个人简介:杨暖,河南确山人。中山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生,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佛山文学院签约作家。山野间长大的80后女子,客居南方10年,多年沉迷中国古典文化的情怀,在书卷与自然中,返璞归真,安静守拙。陆续在《羊城晚报》《珠江时报》《井冈山报》开辟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