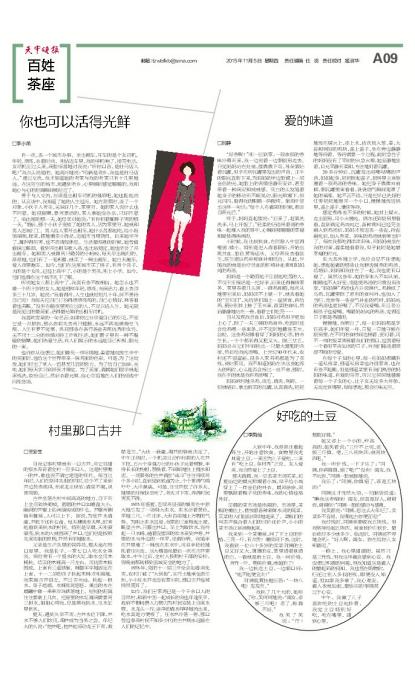□王安生
自我记事村里就有一口古井,用它甘甜的泉水养育着全村一百多口人。这是村里唯一的井,谁也说不清它建造的年代。每当过年时,人们在祭拜先祖的同时,总少不了来到井边焚香跪拜,祈求龙王保佑:清泉不竭,风调雨顺。
古井坐落在村中间高高的地方,自下而上全用砖块砌成。圆圆的井口如磨盘大小,幽深的井壁上长满绿绒绒的纤毛。井壁两侧留有脚窝,人可以上下。据说,为使井水清澈,井底下还有石盘。每天拂晓至天黑,时常能看到来挑水的村民。特别是早晨,天刚蒙蒙亮,挑水的人就围满了井口,他们总是按照先来先取的原则,井然有序地取水。
父亲是生产队里的饲养员,整天泡在牲口屋里。我是长子,一家七口人吃水全靠我。锅灶旁有一个盛水的大缸,取水全用木桶挑。结实的木桶高一尺左右,用优质木板围成,上面有三道铁箍,桶鋬牢牢地固定在上面,十一二岁的孩子挑起木桶才刚离地。我家离古井很近,不过百米远。挑起一担水,身子趔趄,水桶晃晃悠悠,溅出的水在晨曦中像一串串珍珠洒落地上,短短的距离往往要歇上几次。把屋里的水缸灌满需要两三担水,姐姐心疼我,总是帮我挑水、往水缸里倒水。
夏天,遇到久旱不雨,古井水位下降,井水不够人们饮用,淘井成为当务之急。年纪大的人说:“挖井吧,挖井能惊动龙王下雨,救助苍生。”大伙一商量,淘井的事就决定了。中午正热时,一个机灵且动作利索的人在井下挖,五六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光着臂膀,手持长长的钩担,替换着、不间断地往上提水和泥。一场紧张的古井清淤“战斗”往往持续两个多小时,直到见到底盘为止,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可是,往往井挖了许多天,地里的庄稼快旱死了,老天才下雨,弄得村民哭笑不得。
1975年盛夏,连续两昼夜的暴雨在中原大地引发了一场特大洪水。洪水泛着黄色,平地三尺,一片汪洋,大有吞噬地上万物的气势。为阻止洪水进屋,我家的三面堆起土埂,眼望古井,只露出井口。早上为取饮水,我拎起一只水桶,趟着没腰深的洪水来到井旁,井里的水与外边的一样平,泾渭分明。我随手在井里灌了一桶放在洪水中,用双手轻轻地托着往回走。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在古井里取水,中午过后,全村人按照村干部的安排,傍晚前都转移到县城安全的地方了。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春风化雨,农村打破了“大锅饭”,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小小压水井走进农家小院,那口古井也被悄然废弃了。
如今,我们王家湾已是一个千余口人的自然村,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我也年逾花甲,政府不惜耗费人力物力为村民安装上自来水管。水龙头一拧,洁净的清水哗哗地流出来,吃水真是方便极了。压水井冷落一旁,那口曾经奉养村民不知多少代的古井则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