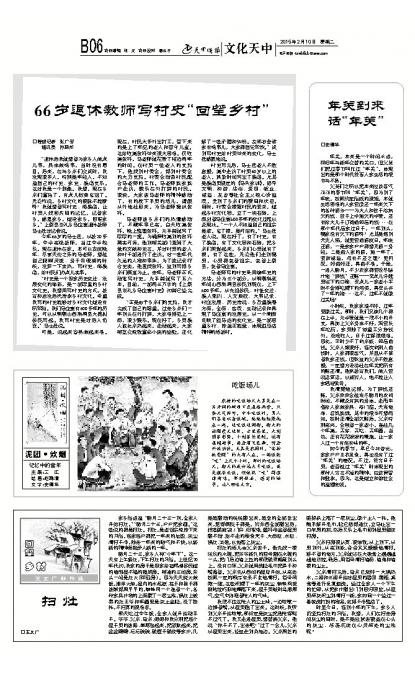□史建华
年关,本来是一个时间术语,即旧年与新年交替的关口,但父辈们把过春节叫作过“年关”,体现出的是那个时代贫苦人家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父辈们之所以把本来应该喜气洋洋的春节叫“年关”,因为到了年底,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本就生活困难的人家要偿还一年来欠下的各种债务——为大人和孩子治病欠的钱、孩子上学拖欠的学费,还有给大儿子订婚借邻居的钱……在那个年代居家过日子,一年到头,哪家没有欠下的债呀?尤其是遇到天灾人祸,就更要借债度日。年底还债,一是家家户户都想无债一身轻;二是借人家的债,拖一年了,要讲诚信,焉有不还之理?更何况,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于是,一进入腊月,不少农家都要绞尽脑汁地“拼钱”还账——卖点儿牙缝里省下的口粮、卖点儿一家老小平时不舍得吃攒下的鸡蛋,再卖头养了一年的猪……这不,过年不就像过关吗?
小时候,我家家境不好,过年更像过关。那时,我们兄妹几个都在上学,光学费就是一项不小的开支,再加上父亲身体不好,需要长年吃药,家里除了指望工分挣钱外,没啥收入,日子过得很艰难。因此,平时少不了向亲戚、邻居借钱。父亲人缘很好,每次向别人借钱时,人家都很客气,并且从不催着我家还钱,但耿直的父亲不敢怠慢,一定想方设法赶在年关把所有的账还清。他常教育我们,做人要说话算话,以诚待人,绝不能让人家戳脊梁骨。
我清楚地记得,为了拼钱还账,父亲常常会趁寒冬腊月的农闲时间,不顾及有病的身体,走街串巷给人家做家具、漆门窗。天寒地冻、忍饥挨饿,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按时还清全部欠账后,父亲特别高兴,会领着一家老小,连赶几个年集,买穿、买吃、买年画,当然,还有花花绿绿的鞭炮,让一家人过一个有滋有味的年。
如今的春节,早已今非昔比,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再也没有了过“年关”的窘况。不过,贫穷日子里,老百姓过“年关”时体现出的那种人穷志不短的精神,应该保留和继承。因为,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道德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