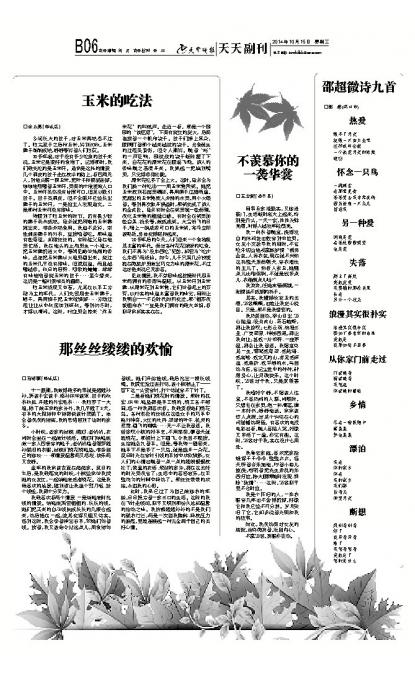□余永亮(驿城区)
乡间长大的孩子,对玉米再熟悉不过了。收完麦子之后种玉米,待到初秋,玉米棒子渐渐成熟,静静等待着人们收获。
20多年前,对于没有多少吃食的孩子来说,玉米已是很好的食物了。记得那时,我们最先吃的是玉米秆。通常是这样的情景:几个调皮的孩子走在放学的路上,看四周无人,到地头薅一棵玉米,把叶子和根部去掉,细细地咀嚼着玉米秆,里面的汁液便流入口中。玉米秆虽然没有甘蔗可口,但足以吸引孩子。孩子虽调皮,但不会破坏已经长出棒子的玉米秆,一是怕主人发现追究,二是那种玉米秆没有甜味。
转眼到了收玉米的时节,仍有极少数的棒子尚未成熟,母亲就把稍嫩的玉米棒挑出来,准备煮熟食用。我迫不及待,索性剥去棒子的外衣,直接啃着吃。那味道有些青涩,却甜丝丝的。有时趁父母在地里忙活,我在地头的土沟里生一小堆火,把玉米棒扔进火中,等闻见略带焦煳的香味,迅速把玉米棒从火堆里翻出来。烧过的玉米几乎没有甜味,但很筋道,而且越嚼越香。秋日的田野、唱歌的蛐蛐、津津有味地啃着烧玉米的孩子……至今想来,这仍是一幅朴素唯美的画面。
收玉米烦琐又辛苦,尤其在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年代,人们先要掰去玉米棒子,晒干,再用锥子把玉米粒锥掉……劳动过程往往从中秋延续到深秋。等到初冬时,才得以清闲。这时,村庄里会传来“炸玉米花”的叫喊声。走近一看,那是一个圆圆的“铁疙瘩”, 下面有烧红的炭火,后面连接着一个帆布袋子。孩子们捂上耳朵,眼睛盯着那个越来越鼓的袋子。美食诞生的过程虽紧张,但令人期待。随着“嘭”的一声巨响,圆鼓鼓的袋子顿时瘪了下来,白花花的爆米花在眼前飞溅,诱人的香味随之荡漾开来。我抓起一把填到嘴里,只觉得香甜松脆。
爆米花吃多了会上火。这时,母亲会为我们换一种吃法——用玉米糁熬粥。她把玉米放到石磨里碾碎,再用筛子过滤两遍,把滤出的玉米糁放入煮沸的水里,用小火煨着。等到再次掀开锅盖时,那粥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母亲有时会在粥里搅一些面糊,淡化玉米糁的粗糙口感。有时会在粥里加些白菜、粉条等,做成咸粥。大雪纷飞的日子,喝上一碗咸香可口的玉米粥,寒冷立即被驱散,身体变得暖和起来。
2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迎来一个食物极其丰富的年代。面对各种花花绿绿的吃食,我们不再为“没东西吃”犯愁,却要为“吃什么东西”而烦恼。如今,儿子只需几分钟便能在微波炉里做出巧克力味的爆米花,不过这对他来说已无惊喜。
见此情景,我不禁回味起孩提时代因玉米而拥有的香甜与温暖。从玉米秆到玉米棒、从爆米花到玉米糁,它们带着泥土的芬芳,以朴实的味道丰富着我的味觉,同时让我明白——不论时代如何变迁,那“粗茶淡饭粗布衣”一直是我们拥有的最大幸福,看似寻常却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