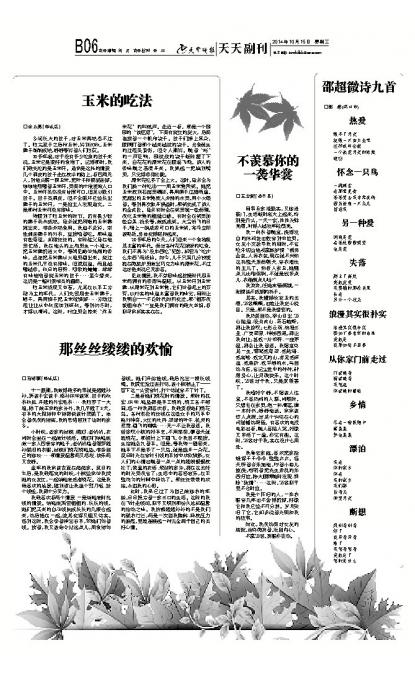□马银丽(驿城区)
十一假期,我做得最多的事就是缝缝补补,拆被子套被子、修补床单被罩、孩子的秋衣秋裤、开缝的外套毛衣……我收罗了一大堆,除了做正常的家务外,我几乎缝了3天,右手的大拇指和中指都快被针顶破了。体会着淡淡的指痛,我的思绪回到了幼时的家乡。
小时候,老家的姑娘、媳妇、老奶奶,农闲时会坐在一起做针线活。媳妇们纳鞋底做一家人四季穿的鞋子,老奶奶端着簸箩缝补破旧的衣服,姑娘们绣花绣鞋垫,准备自己的嫁妆……那情景温馨而又活泼、快乐而又安静。
童年的我常被安置在姥姥家。夏日的午后,是我最落寞的时候,小姨经常带我找她的女友红,一起纳鞋底或者绣花。这是我最喜欢的场景,碰到谁让我递个剪刀啦、扯个线啦,我都十分卖力。
我最喜欢看两个情景:一是纳鞋底时捻线的情景。纳鞋底需要粗粗的、长长的线,她们把买来的白洋线桄成长长的几根合起来,然后搓在一起,使其变得又粗又结实。每到这时,我会争着伸出右手,帮她们勾着线。接着,我又被命令站远点儿,用食指勾着线。她们开始搓线,最后捻出一根长线绳。我慌忙抢过去打结,被小姨制止了——留下这一头要穿针,打个结就穿不了针了。
二是看她们绣花时的情景。那时的枕套、床单、鞋垫都是手工绣的,绣工各不相同,每一种我都喜欢看。我最爱看她们绣花鸟。各种彩色的丝线在这些女子的巧手中格外神奇,火红的牡丹、翠绿的叶子、机灵的鸳鸯、翻飞的蝴蝶……无一不让我着迷。我曾惊叹小姨的好手艺,不用描图,聊着天就能绣花。那银针上下翻飞,令我目不暇接,生怕她会扎着手。但是,等我转一圈回来,她手下不是多了一只鸟,就是盛开一朵花。夏日时光在穿针引线的手指中欢欣跳跃,女人们的心情也随着一点一点的缝制慢慢放松了;繁重的农活、琐碎的家务,都在这美好的时光里淡忘了;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在平整均匀的针脚中释然了。那丝丝缕缕的欢愉,永驻我的心田。
此时,我早已过了为自己做嫁衣的年龄,日日操劳着一家三口的生活。这时的我在飞针走线间,似乎又嗅到那份久远却温馨的怡然之味。我仿佛缝缝补补的不是我们的破衣烂衫,而是一次自我陶醉、释放压力的旅程,更能连缀起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美好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