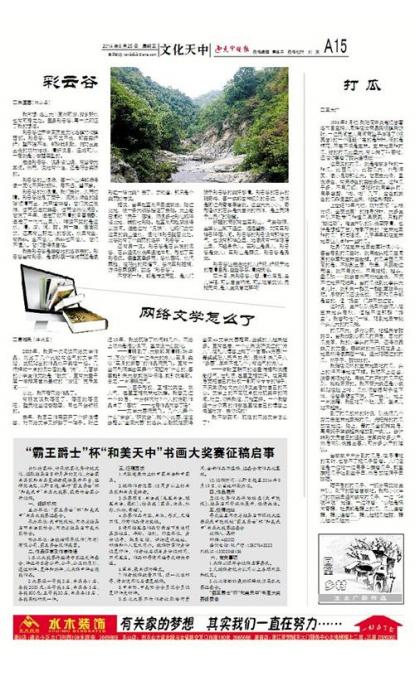□王太广
1996年9月初,我陪同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周涛在汝南县梁祝镇采访时,一位民间艺人用河南坠子演唱了《祝英台》的一个唱段:“高的是秫秫,低的是棉花,不高不低是芝麻。芝麻地里种打瓜,结的打瓜比盘大,有心摘了叫哥吃,还怕你尝着了甜头连根拔……”
这里说的打瓜,就是俺家乡种的一种瓜,比西瓜小,比甜瓜大,外形浑圆,像小足球那么大。它表皮光滑,呈浅绿色,有深绿色的曲线条纹。 这种瓜子多,不用刀切,想吃时就用拳头打,用手掌劈,“嘭、嘭”几下,白色或黄色的瓜瓣便呈现出来,吃起来很甜。
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指导方针,大多生产队不敢专门种植瓜果蔬菜,只能打“擦边球”。俺生产队的队长李芳清,也许是想起了古人传承下来的“芝麻地里种打瓜”那句唱词,几乎年年都在芝麻地里让人点种一些打瓜。
社员们在芝麻地里锄草时很小心,每当看到打瓜苗时,就用锄头把瓜苗周围的杂草和芝麻苗锄掉。打瓜与西瓜不同的是,不挑剔土质,耐旱,只要锄过两遍,就不用浇水,不用施肥、掐头、盘瓜秧……就会自然而然地生长,不慌不忙地开花结果。当打瓜长到比拳头大点儿时,就引来一群又一群割草孩子光顾。尽管打瓜还没长成,瓜瓤和瓜子都是白的,但“馋虫”们并不放过它。
这时候,生产队队长虽然会派人在芝麻地头看秋,但挡不住那群“馋虫”。我曾和他们一样,爬到地里专挑个头儿大的打瓜摘。
打瓜不大,多为沙瓤,吃起来甘甜爽口。当我找到沙瓤瓜打开后,因为打瓜皮厚,我的小拳头打不开,还得依靠镰刀的力量。毒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地里热得像蒸笼一样。经太阳晒过的打瓜,热乎乎、甜丝丝的。
我蹲在闷热的芝麻地里吃打瓜,头上的汗不停地往下掉。我顾不上这些,狼吞虎咽地吃。用镰刀打开的打瓜不规则,豁豁牙牙的。我不管大块还是小块都贴在脸上啃,瓜水顺着腮帮子往下淌,沿着手臂往下流。不一会儿,地上一片狼藉,我已吃了个肚儿圆,差点儿站不起来。
到了打瓜成熟的时候,队长派几个劳力去芝麻地里摘打瓜,先把摘的打瓜放在地边、路上,等打瓜全部摘完后,再用架子车装起来堆放到一块儿。会计韩彩文凭自己的经验,估算共有多少斤,然后向队长提出每人可分多少斤的建议。
当家家户户分到打瓜后,在尽情吃的同时,也忘不了把瓜子留着。人们往往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接着瓜子,或直接把瓜子吐到盆子里,然后放在筛子里晾晒。
晒干后的打瓜子,一部分需交给生产队,剩下的留着自家吃。我和小伙伴们的衣袋里经常装有打瓜子,一边嗑着,一边哼着:“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连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