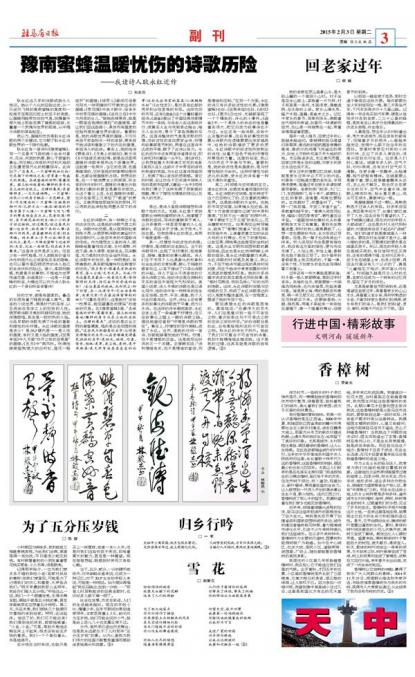——我读诗人耿永红近作
□ 孙友民
耿永红这几年的诗歌成就令人惊讶。她从个人化的经验出发,从一只逆风飞翔的豫南蜜蜂的高度和一粒离开豆荚回归泥土的豆子的角度,以温暖而略带忧伤的气息,抚摸着中原大地上那些充满了痛感的修辞,丈量着一个灵魂与世界的距离,从中揭示诗歌的某些秘密。
我以为,温暖和忧伤是耿永红诗歌的两个关键词,它勾勒了耿永红诗歌世界的一个隐约轮廓。
耿永红有一首诗叫《豫南蜜蜂》,写一个在春天飞翔的微小生命对春天、花朵、河流的热爱,醉心于甜蜜的事业,而它赖以存续的天空和大地却正在遭受现代化的粗暴掠夺。此诗如下:“在春天,一只蜜蜂梳妆打扮/它采摘下的雌性之美/孕育着一场盛大的艳遇。在被蛰痛的田野/雾霾深重。掘土机四肢着地/臃肿的身子伏在土地的皮肤上。恣肆的暴戾/在蜜蜂那里,一次次被稀释。一只蜜蜂/放低小小的身子躺在一片花瓣上,望乡/作为豫南的一只蜜蜂/它痴爱的柳叶河/已挤不出一滴泪/潮湿的抒情凉薄于人情/一只蜜蜂飞呀飞/繁多的赞美堆垒在头上,花香弥漫/那时,在开满花朵的村庄/她小小的身子经过榆钱,经过槐花/经过春风打磨//这些年,她采摘下来的人事/在柳叶河两岸,透着馥郁的芬芳/村庄凋谢。树木肃立/多年以后/脚步逆流而上,看见一只豫南蜜蜂飞过浩渺的/天空,化成一朵绢花/别在故乡的鬓角。”这首诗当然是多义的。但至少有一种可能是,对人类既有价值与冰冷的现代化之间紧张关系的隐喻,也可以看作是四顾茫然的诗人自己的生存状和历险记。微小、柔弱而敏感,热爱春天的事物,不倦地为世界传递花香,创造美好……这是一只蜜蜂的标签,大概也可以作为诗人耿永红的一个身份标签来看待!
一
好的文学,都是有温度的。鲁迅的东西有着刀锋般的逼人寒气。莫言的小说世界,满是时代的苍凉,以及流淌在苍凉之上的怒放的人性。俄罗斯诗歌月亮的阿赫玛托娃,她的深情歌唱,其实是一腔炽热的火焰。北岛早期的诗歌充满了冷峻的意象和理性的冷抒情。永红诗歌的温度是多少?是
二
永红的诗歌中,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淡淡忧伤,这是她的诗歌气质之所在。诗歌中的伤感,是从屈原到杜甫到陈子昂,从俄罗斯诗歌的黄金时代到白银时代,以致百年来的中国新诗的传统。作为理想主义者的诗人,眼睁睁地看着传统式微、乡村凋弊、河流干涸、亲人凋零、容颜老去、花朵飘落,无力感和忧伤总会油然而生。永红诗歌中的忧伤,是一种明亮的、有疼痛感的,具有歌唱意味和古典情怀的忧伤。“很多影子/像暮色里熟透的果实,落入尘埃/无形无声。而我/作为这暮色里最后一枚青涩之果/等待黎明的光泽,指引我作别旁逸的枝桠?/去往晨露的故地,洗却风尘/卸下仰望,在一汪清凉中/完成由青转黄,由黄及紫/只在最后保留带刺的核仁”(《暮色苍茫》),这是她对“没有一枚果实,能回避暮色的侵染”的宿命的叹息。在《豫南蜜蜂》里,“在被蛰痛的田野/雾霾深重。掘土机四肢着地/臃肿的身子伏在土地的皮肤上。恣肆的暴戾”,述说的是农业文明的黄昏景象,唱的是古老田园的挽歌。“这些风不断翻卷的名字/从明亮变得黯淡的名字/从晶莹璀璨变得暮色斑斑的名字/是祖先,祖母,外婆,母亲,姐妹/是草,是尘埃,是树,是中原麻雀/是光阴背后层层垒垒的白骨/这些先后凋零的落英/沁满胭脂水粉”(《女性史》),是对易老红颜的凭吊和女性苦难的书写。这样忧伤的书写,还有《追鱼》这个分量较重的组诗。《追鱼》牵出了中国经典戏剧情节中的一条线,与母亲人生这条线并行,使真实人生与戏剧表达暗合,暗示人生如戏,展示了某些残酷的东西。这首诗整体的气息是浓郁的抒情,但叙述性的言说贯穿全诗,抒情和叙事都是节制的,两者在这首诗中达成的平衡,赋予了此诗以张力。永红的近作中还有两首诗值得关注,即《游戏》和《邂逅一头牛》。读《游戏》,让我想起意大利导演贝尼尼的电影《美丽人生》,这部片子中带泪的游戏所制造的荒诞,与永红这首诗异曲同工,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悲剧感。读它的时候,总让你在不忍卒读中体味人性的柔软和坚硬。《邂逅一头牛》同样向我们展示了这种充满了悲剧感的残酷,展示了理性与情感的悖论以及诗人的无奈。
三
表达,是诗人呈现诗歌理想和诗歌个性的方式。无疑,永红是个受到缪斯女神特别垂顾的诗人,她掌握了诗歌的密码,写诗的禀赋异于常人,让许多像我一样苦苦写着的人心生嫉妒。而这关乎才情,关乎技术,不说也罢。但我觉得永红的表达,有两个维度值得一提:
其一,抒情性与叙述性的共振。抒情性,是诗歌的古老胎记。当下的诗歌写作,出现了反抒情的,拒绝象征、隐喻、意象的叙事化潮流。诗人们乐于书写个人化具象化的形象和社会生活的日常场景,醉心于细微的感官反应,以至于推动了口语化诗歌的兴起。诗人于坚从不讳言他的口语化诗歌立场,他的诗总是在流畅和平实的言说中呈现大气和深刻。美国小说家、诗人卡佛的诗歌也是口语化写作,他的诗中有一种特有的活生生在场感,自然、平实、清澈,我个人对此印象深刻。当然,诗坛上还有更多的叙事化的诗歌流于平庸,成为口水诗。在这样的诗学潮流面前,永红总体上走了一条偏重于抒情性,但又在叙事化上踏上一脚的诗歌之路。据说她曾经宣称“抒情是诗歌的琴弦”。事实上,抒情性的写作策略,成就了永红。当然,读她的任何一首诗,你都能够看到她的节制。抒情,但不是情感的泛滥。这是她写出好诗的又一个关键。正像韩东说:“诗和情绪有关,但不是情绪的宣泄,而是情绪的压制。”在另一个方面,永红的诗又有许多叙述性的元素。《豫南蜜蜂》也好,《豆荚来信》也好,《游戏》也好,《更衣记》也好,无疑都呈现了一个个精致的、诗化的小事件。《追鱼》中,一个具体人的命运的信息量着实很大,把它归类为叙事诗也不为过。永红还有一些诗歌,没有什么完整的叙事,但总有叙事性的场景从诗歌内在逻辑需要出发穿插其中,给她的诗歌增添了更多的灵动。永红诗歌中的叙述性所放射出的诗性,丝毫不逊色于她的抒情性所展现的力量。这里的秘密,我以为仍然在于平衡与节制。重要的是,她的叙述性是有温度的,是与抒情性相依为命的。这种抒情性与叙述化的共振,使永红的诗有着一种说不清的丰富性。
其二,时间感与空间感的互交。读永红的诗,总感觉有着很强的时空感。永红诗歌的空间感,首先特定于这个已经物化了的、正在重新洗牌的世界。这是她诗歌的大坐标。在她的书写空间里,如果镜头拉近些,就是“十万亩麦田替你辽阔”的中原和豫南,“已挤不出一滴泪”的柳叶河,“亭子悬挂于三千云烟”的老乐山,花朵馥郁的村庄。如果再拉出特写镜头,就有了“麦穗们抵着头”的五月里的田地中央、上演着悲喜交加的命运大戏的乡村舞台、月光下的麦秸垛,以致豆荚、棉桃等这些微观的坐标刻度。这是农业文明和田园牧歌的最后阵地,因此也是永红向神明献上诗歌的祭场,是永红诗歌摩擦力来源。永红诗歌的时间感及其意义,我以为,不在于她诗句里出现的具体时间刻度,而在于她诗中常常流露的对时光流逝的敏感和叹息。她的许多诗篇中讲述的其实都是光阴的故事,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似的光阴的挽歌。这样,永红诗歌时间感与空间感的交叉,构成了永红诗歌表达的切入角度和整体基调,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的书写个性。
要说清楚永红的诗歌是困难的。桑塔格说:“在最伟大的艺术中,人们总是意识到一些不可言说之物,意识到表达与不可表达之物的在场之间的冲突。”好的诗歌总是如此,总有桑塔格所说的不可言说之物。耿永红的诗也不例外。她给了我们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诗意,我却不能精准地去描述她。这不是我的过错,这其实就是诗歌的自有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