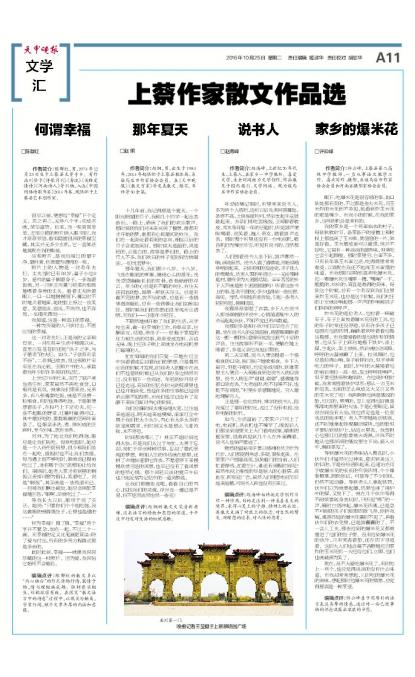亚洲第一门
晚报记者王莹摄于上蔡蔡明园广场
何谓幸福
□陈群红
作者简介:陈群红,男,1974年12月23日生于上蔡县无量寺乡。有作品刊登于《诗歌月刊》《奔流》《关雎爱情诗》《河南诗人》等刊物,入选《中国网络诗歌年鉴》2014年卷,现供职于上蔡县艺术创作室。
很早以前,便想给“幸福”下个定义。思之再三,无非八个字:功成名就,荣华富贵。后来,当一张简简单单、近似白描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我才渐渐领悟,看似隐匿很深的幸福宝藏,其实并无多少玄机,它一直鲜活地展现在我的眼前。
这张照片,是我拍摄过的最干净、最朴素、色调最为透明的一张。
照片上的人物是一对老年夫妇。丈夫当时已有88岁,妻子小他8岁。慈祥的妻子侧着身子,一手端着饭碗,另一只手正用羹勺轻柔而细致地喂着身旁的丈夫。看着丈夫眯着眼儿一口一口地慢慢咽下,脚尖时不时地点着地面,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笑意。笑意很淡,很浅,不热烈,也不奔放,一如春花微绽……
我知道,这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一种为所爱的人只求付出、不图回报的幸福。
这一对老夫妇,正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一对在艰辛生活中相濡以沫,直至白发苍苍时还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夫妇。如今,“子欲养而亲不待”,二老俱已故去,但这张照片牢牢压在我心底。因照片中的人,承载着我年少时许多美好的记忆。
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虽然不再吃食堂,口粮终是有限。就拿我们家来说,兄弟多,有八张嘴要吃饭,就是不浪费一粒粮食,有时也难得吃饱。于是娘便想着法子,在技巧上下足功夫,把一些不起眼的野菜、红薯叶做得可口。其中最好吃的,要数娘做的芝麻叶面条了。经娘亲手洗、煮、晒制成的芝麻叶,至今回味,犹有余香。
另外,为了能让我们吃得饱,娘总是让我们先吃。每到吃饭时,她总是一个人待在厨房里,很少和我们坐在一起吃,盛饭时也不让我们去盛。每当遇上饭不够吃时,娘就说已提前吃过了,遂将属于自己的那份让给我们。刷锅时,她老人家才将锅里的剩饭以丢掉可惜为借口,笑着吃了。说是“剩饭”,其实就是一些残渣而已。一旦被我们瞧出破绽,她总会满脸幸福地回答:“娘啊,早就吃过了……”
等我长大以后,娘终于说了实话。她说:“只要你们个个能吃饱,我这做娘的就算饿肚子,心里也是甜的……”
何为幸福?算了算,“幸福”两个字并不繁杂,加在一起,不过二十一画。而幸福的定义比笔画更简洁:除了爱与付出,所有的多元方程算式都是多余的。
此时此刻,幸福——就像我深深珍藏的这一帧照片。因为爱,我深信它始终不会褪色。
编辑点评:陈群红的散文多以“内心独白”的形式借物抒情,寓情于物,情与理相映成趣。取材虚实相生,结构疏密有致。在探究“散文语言中的诗意”过程中,以现实为触角,字里行间,赋予文章丰厚的内涵和意蕴。
那年夏天
□赵 炯
作者简介:赵炯,男,出生于1984年,2014年起供职于上蔡县教体局,系驻马店市作家协会会员。在《天中晚报》《散文百家》等发表散文、随笔、书评等50余篇。
十几年前,我记得那是个夏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几个同学一起出去游玩,一路上,洒满了我们的欢乐歌声。那时侯的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谁都有才开始的梦,谁都有心底最初的向往。我们在一起谈论着将来的志向,相信以后的日子会更加美好。那时侯天是蓝的,风是轻的,云是白的,故事是梦幻的。路上的行人不多,我们欢乐的样子使时间仿佛凝固,一切恍若梦中。
那年夏天,我们都十八岁。十八岁,飞扬在眼底的柳絮,缠绕心头的落花;恍恍惚惚幽幽长长的雨巷,卷卷舒舒的浮云。年少的心总是有不羁的向往,向往天涯孤旅的愁,渴慕一醉到天尽头。总是有做不完的梦,饮不尽的酒,总是有一些情愫潜滋暗长,总有一些偶像让我们如痴如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还很单纯而且透明,而我们——正值年少轻狂。
不期然地就开始了我们的生活,从学校出来,做一份平常的工作,侍奉双亲,应酬亲友,结婚,带孩子……屈服于家庭的压力和生活的琐事,渐渐变成发胖、言语无味、晚上把孩子哄上床就坐在电视机旁打瞌睡的人。
忙忙碌碌的我们日复一日地在红尘中执着着或忘却着我们的梦想,只是蓦然回首的时候才发现,时间老人的脚步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已从我们的身边悄然而过,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年轻的岁月似乎已经走远,美好的回忆在时光的荒漠里也已经开始淡化,曾经许多的往事都已经烟消云散不见踪影,而我们也早已没有了安静下来独自面对内心的时间。
我们总嫌时间太瘦指缝太宽,过往越来越遥远,明天越来越模糊,滚滚红尘中属于我们的太少太少,内心有太多太多的欲望和需求,而时间又永是那么飞速流转,永不停息。
时间都去哪儿了?其实不是时间走得太快,而是我们太过于匆忙,太善于忘却,匆忙于浮世种种琐事,忘却了最初单纯的梦想。明知人生的终结就在那里,还拼了命地快速朝它奔去,不愿意停下来慢慢欣赏沿途的风景,也早已没有了看风景的悠然心情。那个风轻云淡的夏日午后也只能定格为记忆中的一道风景线。
让我们都慢些走吧,看看自己的内心,找找我们的灵魂,浮世走一遭已是不易,何不悠然淡然怡然一些呢!
编辑点评:赵炯的散文文笔清新典雅,追求语言的精致和思想的深邃,于平淡中抒发对生活的细腻感触。
说书人
□赵海峰
年幼依稀记事时,村里常来说书人。多为两个人搭档,进村以后先询问落脚处,条件不高,土房柴屋均可,然后支起牛皮鼓敲起来。乡亲们刚吃罢晚饭,正闲聊着收成、雨水等年复一年的话题时,听见鼓声便吆喝着,说笑着,拖儿带女,循着鼓声走去。那时整个村里还没有一台电视机,收音机仍为稀世珍宝,听见有说书的,自然都去了。
人们围着说书人坐下后,鼓声骤然一响,满场寂然。说书人清了清喉咙,开始似唱非唱说起来。王侯将相的发迹史,才子佳人的鸳鸯戏,贫困人家的孝贤话……无论哪种题材,最终多为大团圆结局。辛辛苦苦的乡下人不就是图个团团圆圆吗?听着这些书上的事,苍老干涸的心多少也得到一些抚慰、滋润。当然,中间也有曲折处,引起一些老人轻轻叹息、频频拭泪。
夜露渐渐潮湿了衣裳,乡下人在说书人抑扬顿挫的评说中,心情随着剧中人的命运起起伏伏,不知不觉已鸡叫数遍。
我那时多是和小伙伴们早早抢占了位置,坐在说书人的皮鼓跟前,瞪着眼睛瞅着这一颤一颤的玩意缘何能发出底气十足的声音。往往故事听不到一半,便躺在地上睡着了,多是父亲把我抱回家的。
第二天早晨,说书人便会提着一个盛粮食的口袋,挨门挨户地收粮食。乡下人虽穷,但挺守规矩,约定俗成似的,到谁家里主人便舀一大碗粮食倒进说书人的口袋里。说书人则连声“谢谢、谢谢”,感激地背着口袋走去。“大老远的,吃不好睡不好,也挺不容易的。”村里乡亲感慨地说。穷人最能理解穷人。
正是那一位位质朴、博学的说书人,陪我度过了童年的时光,走过了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的时代。
如今,生活富裕了,家家户户用上了电,电视机、洗衣机也不稀罕了,晚饭后人们都坐到屋里关上大门看电视剧,晴朗的夏夜里,很难再见到几个人在外面蹲着。说书人也销声匿迹了。
物质的富裕似乎要以精神的贫乏作为代价,人们都变得焦虑、多疑、紧张起来。在家家户户围墙高筑、狼狗看门的当前,人们忙着挣钱,忙着生计,谁还有闲暇时间呢?虽然电视上播放的尽是恼人的心脏病、高血压、抑郁症广告,虽然人们埋怨电视节目越来越糟,可说书人再也没有回来过。
编辑点评:赵海峰始终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修炼,目的是达到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求得心灵上的宁静、精神上的永恒。其散文充满了对故土的依恋、对自然的赞美、对理想的追求、对人性的思考。
家乡的爆米花
□许云峰
眼下,吃爆米花是很容易的事,街口到处都有卖的,不过都是些大米花,用玉米炸的米花倒不多见,能看到炸玉米花的更是稀少。而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这样的机会是常有的。
我的家乡是一个两面临水的村子,每到秋收时节, 各家各户的屋檐上和树杈上都挂满了玉米棒,黄澄澄的一片,煞是好看。玉米磨成面可以做馍,但并不好吃,它虽有一种淡淡的甜香味,但常吃它会引起胃酸。那时家里穷,白面不多,只有长年靠玉米面过活,吃得胃里常常难受,以致现在我还不能闻玉米面馍的味道。而我那时却特别喜欢吃爆米花,把一颗爆米花往嘴里一撂,“嘎嘣”一下,脆脆的,松松的,简直是难得的美味。每到这个时候,总有一个老汉到我们这里来炸玉米花,也总是这个时候,我们村庄的上空就会响起那一声声的炸响和孩子们阵阵的欢呼声。
炸米花的是位老人,他拉着一辆破车子,车子上面放着爆米花花的工具,他的车子时常还没停稳,早有许多孩子已经围在他的四周,蹦跳着欢呼着看他搬这搬那。而我最爱看的是他烧炉时的情景,他从车子上麻利地搬下铁炉,添上煤,生起火,架上铁锅,然后就拉动风箱,呼呼的火苗就蹿了上来。拉风箱时,他总是拉得山响,身子前仰后合,似乎非常吃力的样子。此时,炉中的火苗随着他的前后推拉一高一低,发出呼呼的响声,似乎要把铁锅吹跑似的。在他烧炉的时候,我常常围着铁炉寻思:那么一点玉米倒进去,出来的怎么竟成又大又白又香的玉米花了呢?我再瞅瞅他满是皱纹的脸,红红的,黑黑的,忽儿觉得他好像是哪部电影里面的大仙,于是心里断定,虽说世间没有大仙,但他肯定也是一位变戏法的能手吧!老人不停地转动铁锅,还不时地拿起铁棍翻动煤块,他的脸似乎要贴到铁炉上,钻进火里去。我曾担心他那红红的脸要被火烤熟,汗珠不时地从他那深深的皱纹里往下淌,滴入火中,瞬间蒸发了。
等到爆米花的香味钻入鼻孔时,小伙伴们才猛然回过神来,意识到来这儿的目的,于是纷纷活跃起来,迅速站在用于收爆米花的长长的布袋四周,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等了不少时间,仍然不见动静。等到老头儿拿起铁筒,伙伴们以为就要起爆,结果他捅了捅炉中的煤,又放下了。就在几个伙伴等得不耐烦要转身去玩时,只听见“嘭”的一声,瞬时白烟冲起,爆米花四溅,已是急不可耐的孩子们旋即四散飞奔,你挤我喊,溅落四处的爆米花霎时不见了,再看伙伴们的衣兜里,已是鼓囊囊的了。不一会儿工夫,那些抢到的爆米花又都被塞进了他们的肚子里。没有抢到爆米花的伙伴,只有哭丧着脸,还在四下寻觅着。这时大人们也会毫不吝惜地把自家炸的玉米花抓一大把给他们,立即,他们也就破涕为笑了。
现在,我不大爱吃爆米花了,有时吃上一两个,也总觉得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而我却常常想起,儿时吃的爆米花的滋味,想起那时抢爆米花的情景,总觉得那真是一种享受。
编辑点评:许云峰善于用质朴的语言表达真挚的情感,通过对一些已逝事物的怀念流露出浓浓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