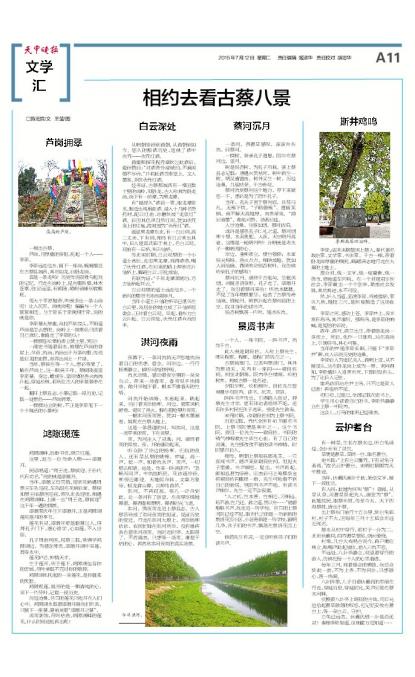□陈宏宾/文 王莹/图
芦岗拥翠

高高的芦岗。
一相出古蔡。
芦岗,用厚重的身躯,托起一个人——李斯。
李斯远走他乡,留下一座岗,蜿蜒横亘在古蔡县城西,其形如龙,曰卧龙岗。
真是一条龙吗?历史传说很难勾起我的记忆。行走在岗岭上,见沟壑纵横,林木苍翠,驻足远望,有郎陵、嵖岈诸峰尽收眼底。
偌大个平原地带,咋就多出一条山岗呢?让人沉思。岗就岗吧!偏偏与一个人紧紧相连。生于斯长于斯掩埋于斯,说的就是你。
李斯墓太厚重,我找不到坟头,不知道芦岗是怎么想的。岗岭上一抹翠色只顾着自己贪玩,谁偷走了李斯的头?
一棵棵苍松翠柏肃立黄土里,哭泣!
一部史书随着泪水,被埋在芦岗的脊梁上,孕育、流淌,流淌出千万条沟壑,传说是巨龙的血管,滋养出岗上一片绿。
当年,蔡侯在等一个人,想必等累了,躺在芦岗上,这一眠竟千年。蔡侯陵遥望李斯墓。身边,蟾虎寺、望河楼的香火冉冉升起,穿越松林,将两位古人的手紧紧牵在一起。
翻开上蔡县志,小篆记载一段历史,记载一处景色——芦岗拥翠。
一棵棵站立的树,不正是李斯笔下一个个鲜活的小篆吗?
鸿隙现莲
鸿隙湖畔,浩渺千顷,映日红莲。
这里,诞生一位传奇人物——漆雕开。
民谣唱道:“周王送,蔡侯迎,子孙代代有功名。”说的就是漆雕开。
当年,漆雕父母完婚,迎亲花轿遇周景王车队巡视,车队跟在花轿后面。蔡侯知景王临蔡国巡视,带队北去迎接,相遇在鸿隙湖畔,上演一出“周王送,蔡侯迎”这千年一遇的情景。
漆雕家次年生下漆雕开,正是鸿隙湖莲花盛开的季节。
莲花有灵,漆雕开更是聪慧过人,拜师孔子门下,潜心修学,心如莲,不入世俗。
孔子周游列国,居蔡三载,常讲学鸿隙湖边。为感念师恩,漆雕开湖中采莲,葬身水中。
莲花妒忌、钟情天才。
生于莲开,死于莲下,鸿隙湖包容你的忠诚,荷叶承载不完对你的敬仰。
鸿隙湖水托起的一朵莲花,是你温柔的笑脸。
鸿隙现莲,展开的是一颗清纯的心,采下一片荷叶,记载一段历史。
历经沧桑,昔日的莲花只能开在人们心中。鸿隙湖水载着漆雕开离我们而去,只留下一座墓,墓前刻着“漆雕开之墓”。
风雨剥蚀,荷叶枯卷,鸿隙湖畔的莲花,什么时间还能再出现?
白云深处
从明朝崇祯到清朝,从清朝到如今。悠久的酿酒历史,造就了酒中状元——状元红酒。
清康熙探花程元章饮过此酒后,题诗赞曰:“对酒香怜浸琥珀,不画风情不尽诗。”并将此酒贡奉皇上。文人墨客,多饮状元红酒。
经考证,古蔡都城西有一横亘数十里的岗岭,似卧龙,古人称其为卧龙岗,岗下有一深潭,为黑龙潭。
有“福源久”酒店一家,取龙潭泉水,酿造出纯粮曲酒,浸入十几种名贵药材,配以红曲、冰糖制成“龙泉红”酒。后因其色泽自然红润,犹如状元身上的红袍,故被誉为“状元红”酒。
遥望黑龙潭东北,有一白云洞,高二丈余,下有洞,相传有白云常出其中,后人建真武庙于其上,名白云观。观前有一石桥,叫升仙桥。
传北宋时期,白云观里的一个小道士贪玩,走进黑龙潭,闻得酒香,喝了状元红酒,在回来的路上醉倒在升仙桥上,脚踏白云,羽化成仙。
有联为证:“千年龙潭蒸琥珀,万古仙桥起祥云。”
白云观里的道士远走他乡,一个新兴的集贸市场热闹非凡。
当年小道士升仙的桥早已湮灭在白云里,我居住的地方成了升仙桥居委会,正对着白云观。早起,看东方白云升起。白云深处,状元红酒向我招手。
洪河夜雨
夜幕下,一条河流悄无声息地流淌着自己的思想、意念。河岸边,一行行杨柳静立,倾听河流的呼吸。
流水动情,感动着夜空里的一朵朵乌云,带来一场春雨。春雨似乎热情些,敞开怀地下着,根本不像春天的性格。
河流开始沸腾,水涨起来,跳起来,拍打着夹岸杨柳。河边,船家风帆舒卷,熄灭了渔火,躲在船舱里听夜雨。
一幅洪河夜雨图,犹如一幅水墨画卷,展现在古蔡大地上。
这是一条普通的河,叫洪河。这是一场平常的雨,下在夜里。
雨,为河注入了灵魂;河,演绎着雨的奔放。夜,开始骚动起来。
听众除了岸边的杨柳、归航的渔人,还有草丛里的蟋蟀、蚱蜢。高一声,低一声,和着流水声、雨声,一切那么和谐。远处,传来一阵诵读声:“急峡泻河声,中流挂帆轻。花依遥岸待,柳傍近滩迎。天地孤舟转,文章万象惊。蛟龙群山舞,共醉传青萍。”
洪河,不再孤寂,张九一泛舟到此,让一条河有了欲望,在夜里尽情地舞着,舞得春和景明、舞得时光飞逝。
洪河,携夜雨走进上蔡县志,古人那首诗成了洪河夜雨的见证,见证历史的变迁。行走在洪河大堤上,两岸杨柳依依,农民忙碌在洪河两岸,没有谁再去在意洪河夜雨。我时走时停,太阳落了,不肯离去,只想等一场雨,淋湿干枯的心,再赏欣洪河夜雨的真实场景。

今日洪河。
蔡河沉月
一条河,携蓍草感叹,滚滚向东流,曰蔡河。
一棵树,秉承孔子遗愿,陪伴在蔡河边,望月。
树是银杏树,为孔子所栽。据上蔡县志记载:唐遇火焚枯死,树中新生一树,明又遭雷击,树外又生一树,历经沧桑,几度枯荣,千古奇观。
蔡河流到蔡沟这个地方,停下来歇息一下,想必是为了陪伴孔子。
当年,孔夫子困于蔡沟店,兵荒马乱,无粮下炊,“子路借粮”,遗留笑柄,竟不解天高地厚,肉香屎臭。“颜回食墨”,难能可贵,贤者回也。
人世沧桑,往事如烟,蔡河依旧。
或许是感恩孔子仁礼之道,蔡河烟柳十里,水美鱼肥。入夜,天空明月高悬。这哪是一轮明月呀!分明就是老夫子一颗明亮的心。
岸边,垂柳肃立,楼台敬仰;水面银光烁烁、渔火点点,相映成趣,犹如人间仙境。微风吹动银杏树叶,我仿佛听到孔子的感叹!
蔡河沉月,演绎千古绝句。华夏风烟,尚留圣贤身影。孔子走了,漆雕开走了。我沿着蔡河来啦!听流水潺潺。不见了当年物景繁华,远去了古蔡传奇仙境。那轮月,照例升起在蔡沟店的上空,找寻当年的读书声。
银杏树飘落一片叶,随水东流。
景贤书声
一个人、一座书院、一阵书声,流传千古。
此人就是谢良佐,人称上蔡先生,师从程颢、程颐,是程门四先生之一。
古蔡城南门,过去叫景贤门,其外为景贤关,关内有一座祠——谢良佐祠。祠坐北朝南,院内亭台楼阁,松柏树木,构成古蔡一处名迹。
夕阳夕照,松柏相伴,良佐先生悠闲漫步在院内,读书、沉思、领悟。
阵阵书声传出,引得路人驻足。仰慕先生才学,更有拜访者络绎不绝,还有许多村民把孩子送来,接受先生教诲。
宋元时期,改谢良佐祠为上蔡书院。
历史记载,元代全国有41所著名书院,上蔡书院便是其中之一。这个书院,源自一位先生——谢良佐。书院的精气神吸收先生毕生心血,有了自己的灵魂。先生那孜孜不倦的读书神情,时时感召后人。
相传,明朝上蔡知县郎兆玉,一日夜闻书声,循声来到谢良佐祠,但见夫子塑像,书声顿息。复出,书声再起。郎知县甚为惊奇,回去后马上筹集资金将谢良佐祠重修一新。先生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新居,但院内书声不绝。有读书声相伴,先生一定不会寂寞。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循着琅琅书声,我走进一所学校。昔日的上蔡书院已经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所崭新的景贤花园小区,小区旁新建一所学校,窗明几净,孩子们的书声,飘荡在景贤花园上空。
倘若先生有灵,一定会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
斯井鸡鸣

李斯故居旧址碑。
李斯,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人,秦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书法家。千古一相,带着卧龙岗厚重的嘱托,踌躇满志地行走在大秦的土地上。
废分封,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修驰道车同轨。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社会,李斯做出一个个创举,助推社会发展,其功其迹,永不可没。
然,奸人当道,陷害李斯,终被腰斩,家灭九族,地挖三尺,是制度酿造了这场血案。
李斯之死,感动上苍。李斯井上,夜半常有鸡鸣,其声凄厉。那鸡鸣,是李斯的呐喊,是冤屈的诉说。
酉年、酉月、酉日出生,带着卧龙岗一身泥土。死后,化作一只雄鸡,站在高岗上,引颈哀鸣,其心可鉴。
当年的井随李斯长眠,只留下“李斯井”碑,向人诉说历史的沧桑。
李斯后人为追忆先人,清明上坟,从不留坟头,这在卧龙岗上成为一景。询问得知,李斯遭奸人迫害而死,下葬时没有头,为了让后人记住。
雄鸡依旧站在井上鸣,只不过是斯人已逝!再也听不见。
功归功,过是过,全部记载在史书上。
学生用心读着自己的书,李斯井静静立在上蔡一中院内。
这会儿,打鸣的雄鸡已经睡去。
云护蓍台
有一种草,生长在蔡水边,听白龟诵经、念卦而有了灵性。
草便是蓍草,草拥一台,取名蓍台。
史书载:“上有白云覆元,下有灵龟守者焉。”故名云护蓍台。宋明时期即为天中胜迹。
当年,伏羲氏画卦于此,始创文字,留下一段佳话。
有人问:此地为何叫“蔡”?查阅,从草从祭,用蓍草祭祀先人,演变为“蔡”。此地居民,取蔡而姓,传至今天。天下四海蔡姓,皆出于蔡。
出上蔡东门前行十五公里,到白龟庙村,村子不大,因每年三月十五庙会而远近闻名。
蔡水从村中穿行,将村子一分为二。北有伏羲祠,祠内蓍草葱郁,烟火缭绕。
村南,几台大戏唱古说今,商户摊位林立,吆喝声此起披伏,游人川流不息。
不远处,八卦亭静立,观望着穿行的游人,仿佛把每一个人的心思看透。
每年三月,闻着盛会的锣鼓,我总会到此一游,不为上香、不为问卦,只想散心,图一热闹。
八卦阵里,儿子沿着伏羲氏的思绪在行走,穿越历史、穿越时光,笑声回荡在蔡水河畔。
抚摸着八卦亭上斑驳的古砖,用目光捡拾起蓍草散落的叹息,把记忆安放在蓍台上,等一朵白云。守护。
白龟已远去。伏羲氏那一卦是否还灵?秦相李斯知道,汉相翟方进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