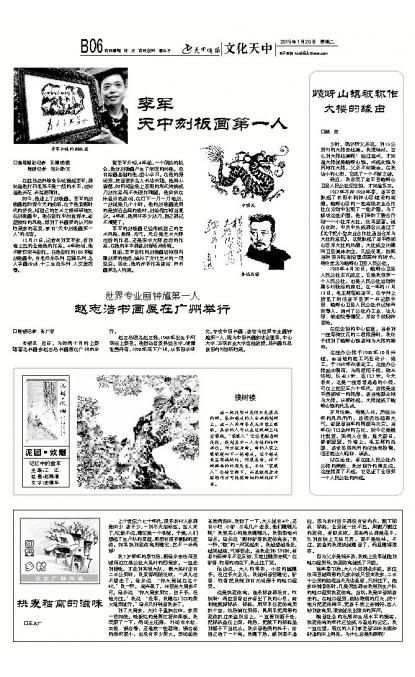回望乡村
□王太广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多农村人家都是床少、被子少,一到冬天怕添客。客人来了,吃饭不说,睡觉是一个难题。于是,人们想起了生产队的草屋,那里有很多铡碎的麦秸。如果拱到麦秸窝里睡觉,岂不一举两得?
我7岁那年的春节后,跟母亲去汝南县城南边红旗公社大吴村的四舅家。一直走到傍晚,才走到果园大队, 距大吴村还有二三公里时,我累得两腿发软,一点儿也不想走了。母亲说:“你大舅就在这个村。”我一听, 高兴极了,非要去大舅家不可。母亲说:“你大舅家里穷,孩子多,没地方住。”我说:“没事,我睡在门口的柴火堆里就行。”母亲只好领着我去了。
到了大舅家,大妗子重病在床,家里一贫如洗。晚饭吃的是蒸红薯和稀饭。我观察了一下,两间土坯房, 外间有水缸、案板、锅台等,还堆放一些器物,锅台前的面积很小,也没有多少柴火。里间前后各放两张床,我数了一下,大人就有4个,还有小收、小驴、三毛几个老表,他们睡哪儿呢?我更关心的是我睡哪儿。我悄悄地问母亲。母亲说:“跟你驴哥拱麦秸窝去。”我一听,“嗷”的一声哭起来 。我越想越难受,越哭越痛,气得要走。当我走到门外时,看看外面伸手不见五指,又能往哪里去呢?在驴哥、收哥的劝说下,我止住了哭。
俗话说,大人的事多,小孩的瞌睡多。没过多大会儿,我就闹着要睡觉。驴哥、收哥把我领到有三间房子的牲口屋里。
说是拱麦秸窝,连条棉被都没有,咋拱啊!两位表哥也许看出了我的心思,麻利地脱掉棉袄、棉裤,用双手在麦秸窝里扒个窑,然后躺在里面,再用手把周围的麦秸扒过来盖到身上,一直围到脖子处,把棉袄盖在上面,最后,把脱下的棉裤垫到脖子下当枕头。我学着他俩的样子,给自己造了一个窝。我睡下后,感到很不适应,因为农村孩子都没有穿内衣,脱下棉袄、棉裤,全身就一丝不挂。用铡刀铡过的麦秸,看似柔软,其实两头都是茬子,扎到皮肤上又痒又疼,很不是滋味。不过,疲惫的我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
因为父亲是饲养员,我晚上没事就跑到牲口屋里玩,拱麦秸窝就成了习惯。
每年春节后,大人小孩都走亲戚。家住汝南县城周围的几家亲戚只要来我家,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当天无法返回 ,只好住下。俺家床铺紧张时,凡是男客都由我领到生产队的牲口屋里拱麦秸窝。当然,我是带着棉被 去的。在牲口屋里,借助微弱的灯光,找个地方把麦秸摊平,把被子放上去铺好,客人钻到被窝里,很快就发出甜美的鼾声。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拱麦秸窝的年代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我一直在想,现在的人们享受着华床美榻和舒适的床上用品,为什么总是失眠呢?
王太广新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