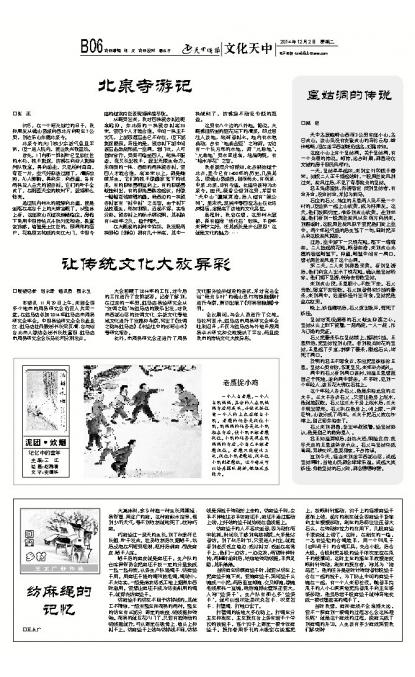回望乡村
□王太广
大集体时,家乡种植一种生长周期短、易管理、用途广的麻。这种麻耐水怕旱,遇到少雨天气,等不到收割就枯死了,故称朽麻。
朽麻经过一夏天的生长,到了秋季秆已长粗、叶子发黄。社员收割后扎捆晒干,然后浸泡在河塘里沤制,沤好后剥麻、漂洗麻皮、晒干入库。
晒干后的麻皮就是麻坯子。生产队的仓库保管员会把麻坯子按一定的分量挽成一挂一挂存放,以备生产队搓绳子、纺麻经子用。用麻坯子搓的绳叫披毛绳,绳劲小,不太结实,一般是做农活或工地上捆绑东西时急用。要想让麻坯子成为结实耐用的绳子,就得先纺麻经子。
纺麻经子的纺车不同于纺棉线的,其做工不精细,一般有整车和简易的两种。整车的纺车有三部分:固定的底座、绕线框和转轴。简易的就五花八门了,只要有能转动的绕线框就行,可以固定在板凳上、墙头上和树干上。纺麻经子上劲与纺棉线不同,纺棉线是靠锭子转动拧上去的。纺麻经子时,左手不停地往右手续麻坯子,麻坯子通过摇动上劲,上好劲的经子就势绕在盘线框上。
纺麻经子的人不喜欢坐着,因为动作简单机械,时间长了感到窝憋得慌,大多是站着纺。到了秋冬时节,只要进入村庄,就能看到老汉或立墙边、或站树旁、或坐在高凳子上,他们一边纺,一边说笑,两臂时伸时扬,两脚时前时后,熟练地转动线框,手舞足蹈,其乐融融。
当纺麻车纺满麻经子时,就要从纺车上把麻经子缠下来。要缠麻经子,需将经子头缠成一小把,而后垂直相缠、交叉相缠,像缠毛线那样一直缠,最后缠得比篮球还要大,人称“经蛋子”。生产队有那么多“经蛋子”,就可以组织社员织粪苫子、织草苫子、打缰绳、打牲口套了。
打缰绳的场地大多在路上。打绳车分主车和副车,主车操作台上备有若干个带钩的铁锭子,每个钩子上固定一根专续麻经子。操作者用多孔的木板套在铁摇把上,按顺时针摇动,钩子上的每根麻经子逐渐上劲,前方的副车就会因麻经子紧缩向主车慢慢移动。副车的后面往往压着大石头,在转动和拉力的作用下,几股麻经子很快就上劲了。这时,在副车的一端,一名有经验的合绳能手,用一个叫瓜子(也叫滑子)的合绳工具,先合小股,后合大股。合股时把各股的经子依次定位在瓜子的棱槽间,这时主车的摇车手放慢速度顺时针转动,副车的操作者,称其为“猪尾巴”,他的任务是逆时针转动着数股经子合在一起的锭子。为了防止中间的麻经子缠在一起,有一个人来回巡视。随着手持瓜子的人小心翼翼地把持着瓜子向主车缓缓移动,他身后若干股麻经子就神奇地变成一根纹理密实的绳子了。
当时我想,麻和麻烦不会离得太远,要不一棵麻到一根绳的过程怎么会这样漫长呢?就是这个麻烦的过程,使麻完成了到麻绳的升华。人生该有多少麻烦需要我们解决啊!
王太广新作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