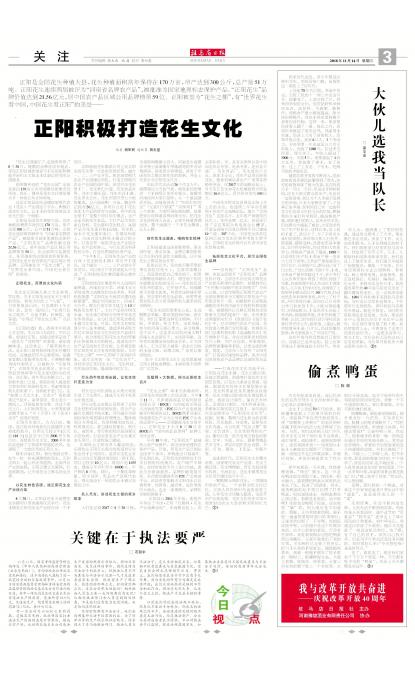陈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而记忆深处的东西任凭岁月长河如何冲刷,总也难以去除痕迹。
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刚刚懂事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落实,使“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那种深藏于肌体内的活力充分释放了出来。当然,我们这些刚入校门不久的学生在父母下地时也不会闲着,或打猪草,或拾柴禾,或到地里帮忙,或者烧锅煮饭……而我因从小患小儿麻痹症左腿落下了残疾,一瘸一拐地往外走自然耽误事,早晨时间短,煮饭的事就落在了我头上。
那年初夏的一天早晨,我烧着稀饭锅,“馋念”顿生,见一只老母鸭夜里在窝里下蛋,便找来一把小锄头,猫着腰把鸭蛋从窝里扒出来洗了洗,投进了饭锅里。其实,盛放鸭蛋的坛子里已经攒了好多鸭蛋,妈妈每放进去一枚鸭蛋都在心里记着,那都是有数的,动不得啊!夜里老母鸭现下的蛋,还在窝里“躺”着,别人绝对是不知道的。倒霉,正当我烧着饭锅,脑子里一遍遍想着即将到口的美味时,父亲突然出现了。不对啊,饭锅还没烧开呢,以前他不是这个时候回来的。由于心里害怕紧张,行动有些异样,我赶紧到锅台边想把鸭蛋捞出来藏好。父亲可能看出了我的反常,不知何时已走到了我身后,把勺子从我的手里拿走,随即瞪视着我。我被一根绳子绑在了院子里的一棵树上,胳膊绑得太高,只能立着脚。姐姐在一旁看着,示意三弟在我的脚下垫上一个小板凳。太阳已升得老高,起早下地劳作的乡邻陆陆续续回家吃饭,我像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耷拉着脑袋,目光不敢和他们相视。
胳膊酸痛,腿也感觉到疲软,脑子里此时一片茫然。不知多长时间,胳膊上的绳子被解开了,“你把他的棉袄找到,给他拿几块馍,叫他去要饭!”父亲吩咐三弟。我走了,拖着瘦小的身影一瘸一拐地走在通往学校的弯曲小路上,我死活没带棉袄,背着的书包里装着的是几块硬硬的凉馍,书本已被掏了下来。半路上,三弟撵上我,把书本给我,那是姐姐特意交待的。中午放学了,我没有回家,也不敢回家,一个人孤单地游走在空旷的校园里。下午一点多的时候,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晚上放学了回家。”我无语,可心里很暖。
是啊,那时候的一个鸭蛋,对我这个穷家来说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油盐”,也是招待客人的一个“菜”。
光阴荏苒,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改善,鸡鱼肉蛋从来客招待、逢年过节的“贵重品”“特享品”逐步走上了城乡居民的日常餐桌。初中毕业后,我通过自学进了乡政府,随后又受邀进了一家县直机关单位,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虽然自己钱不多,但是用于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我经常问儿子:“今天想吃啥?爸爸给你买。”
变了,真的变了,现在我们家和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样,天天都有吃不完的“鸭蛋”,生活上天天都像是在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