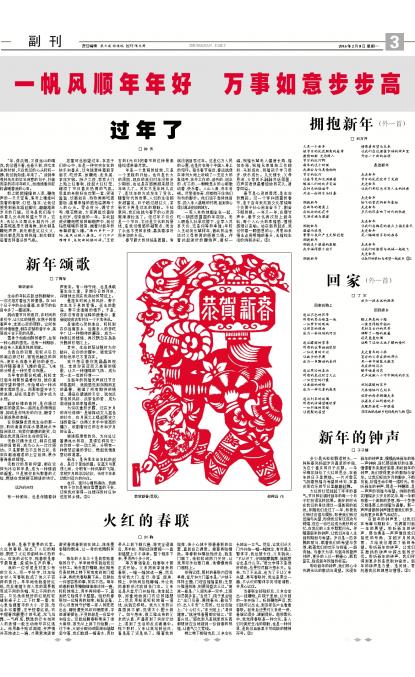□ 刘 静
春联,是春节重要的元素。火红的春联,贴出了人们的期盼,飘进了火红的韵味和火热的心。在我的记忆中,贴春联是春节最隆重、虔诚和庄严的事。 我的一位邻居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写一手好字,过年给全村人写春联就成了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早早地他就备好红纸,然后根据不同人家的需要裁剪成不同的条幅,写上不同的内容。只见他将裁好的红纸轻轻铺到桌子上,上下打量一番,在心里估摸着字的大小、行距,然后半弓着腰,左手按着红纸,右手握着饱蘸墨汁的毛笔,龙飞凤舞,一气呵成,飘逸的行书如同人的表情一般生动地印在红纸上。他用鼻子贴近闻闻,并声情并茂地读上一遍,才满意地颔首微笑着把春联放在地上,阵阵墨香随即飘来,让一旁的我陶醉其中。
每年的大年三十是我家贴春联的日子。早早地母亲就给我们分好工。她负责打糨糊,我们姐弟负责把楼上楼下所有房间的门擦干净,再把老春联撕下来。这貌似一件很容易的事,其实不然。每年的春联都用糨糊细细地涂抹一遍,轻轻地粘上,用手再捋顺一下,直到把它贴得平平整整。贴好的春联如一位娟秀的姑娘,粉脸含羞,尽心尽责地守护着一家人的进进出出,哪怕遭受风吹日晒雨淋,字迹渐渐褪色,不变的却是一份坚守和信念。这就给撕春联带来了很大麻烦,首先从上到下开始撕,一次下来,大部分都还顽固地和墙壁坚守着,我们就提一桶清水,用扫帚从上到下刷几遍,等完全浸湿后,用手抠、用钢丝球摩擦……直到墙壁上干干净净。整个程序下来,要用两个多小时。
等万事俱备后,贴春联才算正式开始。父亲把我拿回来的春联,一幅一幅地读一遍,然后告诉我大门、客厅、卧室、厨房、楼上、杂物间各贴哪幅,并让我把春联依次放到各门边。父亲总是从客厅门开始贴,他拿起上联,郑重地放到门右边的墙壁上,然后用粉笔轻轻地画一道线,说就这样吧。我为父亲的认真感到不解,觉得太小题大做了。如今想来,做工程出身的父亲把认真、严谨落到了实际行动上,落到了生活的点点滴滴中。贴下联时,父亲让我站到远处,看是高了还是低了。随着我的指挥,他小心地平移着春联的位置,直到自己满意。接着再贴横批。等春联和横批贴好后,就是门画了,他轻轻地把门关好,让我用双手拉着门鼻,他慢慢地将门画贴上。
依稀记得,那时的春联内容很单调,客厅和大门基本是:“户纳千祥祥云腾,门迎百福福星照;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厨房一般是:“入厨先净一双手,上案切忌莫多言。”当然了,院子里会贴上“出门见喜、满院春光、勤俭节约、出入平安”之类的。灶台边贴上:“小心灯火。”床头贴上:“身体健康。”就连牲畜圈都会贴上:“家畜兴旺。”感觉到凡是院里的东西都理所应当地接到一份新春的祝福,让喜气久久萦绕。
楼上楼下都贴完后,父亲会长长地出一口气。然后,让我们从大门外开始一幅一幅地念,有时遇上繁体字,我总被卡住,父亲就说:“不认识了,仔细揣摩揣摩,就能意会出是什么字。”语文学得不是很好的我,总要绞尽脑汁想半天。后来,为了不出丑,也为了不让父亲失望,再写春联时,我总是要念一遍,不认识的繁体字向邻居请教,并用心记住。
当春联全部贴好后,父亲会拿出一挂鞭炮,在院子里放,以示新的一年开始了。听到鞭炮声后,我们就可以出去,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春联。回来后还要对父亲讲一讲,看谁记得多、理解得好。潜移默化中,我觉得春联是一种文化,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也是一种传承,是我们血脉里不可或缺的精神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