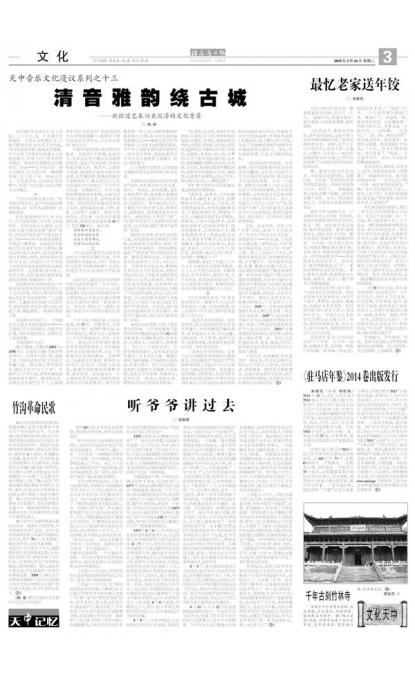□ 谢蔚博
常听80岁的爷爷讲过去的事情,他讲得津津有味,我听后回味悠长。
爷爷生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两年,在洪河岸边的农村度过了饥寒交迫的童年。少年时代,他以一年一斗谷子和一斗秫秫的学费读了几年私塾。西平刚解放,爷爷免费到县城上了中学,一班几十个学生,每周都要自带干粮和烧柴,同学们轮流热饭,到了周末,有时带的干粮发了霉,也得将就着吃。
爷爷大学学的是农业,正赶上大跃进时候,学校响应大炼钢铁的号召,有时几个月在山里伐木,或去水库工地劳动,不经意向别人说了一句:“母亲在家饿得走不动了。”被学校里的工作组知道后,差一点被打成“右派”,毕业被分配到遂平县关王庙公社农技站工作,不久又调到最偏远的石寨铺公社农技站。石寨铺农技站设在离公社几公里远的黄庄庙农业试验场,当时农场有十几个人,十三间草棚,其中两间由农技站使用,一间为办公室,一间是仓库兼爷爷和另一人的住室。站里的主要设备是一支水银温度计、一个上面配发的量雨器、一个自制的风向标。平时的主要工作是参加农场劳动,偶尔也陪着公社领导给群众讲些科普知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爷爷把奶奶从老家接到农场参加劳动,以后有了爸爸、两个姑姑和叔叔。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为了解决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石寨铺公社书记陈少贤要求爷爷协助他大力推广“红薯下蛋”和“棉花营养钵”技术,爷爷全身心投入到这项工作中,粮食高产了,棉花丰收了,爷爷却进了公社造反派的白专道路集训班,还是在陈少贤书记的一番斡旋下,造反派才结束了对爷爷的白专道路集训,后来爷爷回农技站工作,奶奶带着爸爸和大姑去了附近的万庄大队王松庄落户。
1970年的春末,石寨铺公社北部下了一场罕见的冰雹,从凌晨四点到第二天上午九点,爷爷与陈少贤书记步行查看了受灾的六个大队,大部分人要把砸成光秆的棉花、西瓜等作物犁掉,爷爷果断要求他们留下,只犁掉砸毁的春玉米和谷子,结果是西瓜和棉花重新发芽后,获得了与过去一样的收成。
为提高粮食产量,爷爷向公社建议办种子基地,经过批准后,1973年在临近宿鸭湖的老徐庄创办了粮种基地,他带领二十几个从各大队选调的农民技术员,还有刚分来的十几个城市知识青年,烧野草、割芦苇、挖沟渠,硬是在一片荒地上开垦出几百亩种子田,到1975年,全公社基本实现了良种化,取得了亩产平均提高100多斤的好成绩,当时驻马店地区在石寨铺公社召开了粮种繁育现场会。
上世纪八十年代,上级对乡镇七所八站改革,乡镇农技站成了条条不要、块块不管的“无娘孩”,经费、工资被拖欠,职工成了不稳定因素。领导安排已在石寨铺乡里工作的爷爷带领农技站人员搞经营,服务三农,乡里帮助办了经营证,无偿给了门面房,在农技站工作的姑姑对搞经营想不通,奶奶也抱怨他自找麻烦,站里的其他人员也不愿意。爷爷单枪匹马地开始了经营,一边卖化肥、种子、农药,一边指导农户科学种田,局面很快打开,生意十分红火,其他人也被带动起来,这件事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
新世纪初,退休后的爷爷带着奶奶回到了老家西平县,本该颐养天年的爷爷却闷闷不乐,饭吃的少了,人也瘦了许多。还是奶奶了解爷爷,让爸爸在县城旁边给爷爷买了一块土地,种蔬菜、栽花木、育树苗,忙得不亦乐乎;丰收的蔬菜多数送给了亲戚邻居吃,花木也卖了不少钱,小树苗慢慢长大,地也大大升值,奶奶经常唠叨爷爷到了地里就忘记吃饭和休息,说他见了地就没命,爷爷总是笑着说:“我一辈子就爱农业,爱土地,爱干活。”